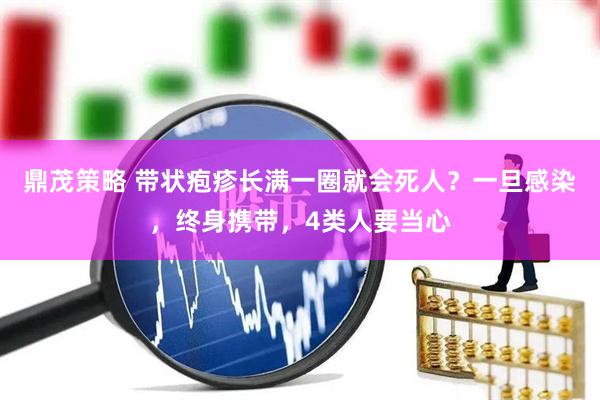潮新闻客户端 国泰平安牛壹佰
假日的阳光,不疾不徐地漫过窗棂,在书案上织就斑驳的光影,连案头积着的薄尘都染上了暖调。我轻轻推开摞得半高的书卷,纸页间飘出一缕陈旧的墨香,便决意要给这书案来场彻底的清理。这方老木案,恰似一座微型时光储藏室,堆叠的岂止是纸张,更是这些年散落在岁月里的思绪、带着青涩的笔触,以及那些未曾宣之于口的心境。
清理的过程,像一场与过去的自己隔空对话。当一沓沓写满字迹的纸被归拢一处,我竟愣在原地——那纸堆足有半人高,后来过秤才知,竟有百来斤重。指尖轻拂过纸面,有的是精心挑选的稿纸,光滑细腻;有的是随手抓来的打印纸背面,还留着报表的残痕;更有些泛黄的旧信纸,边角卷曲如岁月的褶皱。纸上的字迹,时而工整如楷,时而潦草如狂,时而激昂如鼓,时而颓唐如秋,每一笔、每一划,都牢牢锁着某个瞬间的思考与情绪。而这其中,占去大半的,是我那些不成气候的“涂鸦之作”——一篇篇搁浅的草稿,一段段未完成的随笔。
“文能充饥乎?”我望着这堆承载心血的纸,忍不住低声诘问。
展开剩余71%古往今来牛壹佰,多少文人以文言志、以文传情:屈原的《离骚》泣血成篇,字字皆是家国忧思;苏轼的“大江东去”笔落千钧,写尽千古豪情;李清照的“寻寻觅觅”,一纸诉尽半生凄苦。他们的文字,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,即便跨越千年,仍能让后人触摸到字里行间的温度。
再看自己的这些文字,实在相形见绌,真应了那句“唯我写成多病态”。有时为雕琢一句诗,冥思苦想到深夜,抓耳挠腮间写就的,却满是刻意的辞藻与矫情的意境;有时情感泛滥,见风便是雨,落笔成篇后再读,只觉是无病呻吟,既无深度,也少韵味。它们没有前人文字里经得住时光推敲的意境与内涵,反倒像青春期的呓语,或是情绪低谷时的宣泄,带着挥之不去的“病态”——是对文字的过度执念,是对情感的不当放大,更是对创作的盲目狂热。
图片由AI生成。
我将这些“酸臭文”一摞摞理齐,用麻绳捆扎妥当。它们散发出的,不是清雅的墨香,而是混着自我怀疑与尴尬的“酸臭味”。可谁又知,这些纸页上的每一个字,都是我在无数个孤灯相伴的夜晚,一字一句地敲下或写下的。为寻一个精准的词,我翻遍词典;为造一段贴切的句,我反复修改;为表一个模糊的念,我绞尽脑汁——这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心血,曾是我彼时最较真的坚持。
可如今,它们却要“纸上心血论斤卖”。我把纸堆搬到门口废品收购的老阿婆跟前,看着她将纸捆挂上锈迹斑斑的秤,指针颤巍巍停在 “百斤”刻度。秤砣落定,纸被麻利地塞进蛇皮袋,挤压间,那些曾让我辗转反侧的文字渐渐模糊。它们终将被送进造纸厂,粉碎、蒸煮,重归成一张张洁白的新纸,开启另一段循环。那一刻,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,百感交集。
这是一种自嘲,笑自己的文字拙劣,落得这般论斤售卖的下场;这也是一种无奈,在现实面前,未成形的文字竟廉价到只能用斤两衡量;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——把盘踞在书案上、也盘踞在心头的过往彻底清空,让心腾出空间,去装新的思考,去写新的文字。
细想之下,这论斤卖的心血,也并非毫无意义。每一次写作,都是一次笨拙的自我表达,即便不成熟,却让我对文字的运用、情感的把控、世界的认知,多了一分通透。就像学步的孩童,总要在跌跌撞撞中学会稳当迈步,这些“病态之作”,正是我在文学路上蹒跚学步的印记。前人的文字之所以耀彩,是经了时光沉淀、大众检验的精品;而我的这些文字,是创作路上的试错,是成长必然的代价。它们或许没有流传后世的价值,却是我独一无二的成长注脚。
当老阿婆将薄薄几张纸币递到我手里时,指尖触到纸币上的阳光温度,我忽然懂了:这不是在卖废纸,是在与过去的自己好好告别。告别不成熟的笔触,告别矫情的情绪,告别盲目的自信;也是在迎接新的开始——带着这份自嘲的清醒,重新审视创作,以更谦逊的态度学前人精髓,以更真诚的心感受生活点滴,只求未来能写出有分量、有温度的文字,不再让心血沦落到论斤售卖的境地。
阳光依旧明媚,书案已清清爽爽。我坐下,铺开一张新纸,拿起笔。这一次,心里少了浮躁,多了坦然。创作的路本就漫长,自嘲是对过去的反思,而前行,才是对未来的期许。或许有一天牛壹佰,我的文字能摆脱“病态”与“酸臭”,在时光里留下一丝浅浅的痕迹。那时再回头看今日的“论斤卖”,便会笑着认下:这是我与文字相伴时,一段最真实的插曲。
发布于:浙江省淘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